刘大哥叹口气说:“林先生就是孙小姐的未婚夫啊,你们不知道?难怪,她把房子卖给你们,又怎么会跟你们提到林先生。”
胡知道说:“这孙小姐和林先生到底怎么了?”
刘大哥道:“他们也不容易,都是这个城市的外来客,在这里打拼,好不容易在段杏芳手里盘下这个房子,装修了准备结婚,可哪里想到,林先生不知怎么地,居然神经出了毛病,发了疯,谁都不认得了。孙小姐一开始整天以泪洗面的,说是自己买了这个不吉利的房子,害得林先生出了问题,后来我老婆常常去劝劝她,她就也不怎么闹了。书读得多的人,脑子还是蛮通透的,她说要把房子再卖掉,免得什么……睹物思人……说要把卖房子的钱全部给林先生家里,她要离开苏州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回来。”
我说:“那个林先生为什么发疯呢?”
刘大哥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记得他们小两口头天晚上还在我摊子上吃过麻辣烫,第二天就传出林先生疯了的消息。”
周立立说:“胡哥,银子姐,你们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也刚刚住进来没几天,那个孙小姐倒是见过几面,也没看出来神色有什么不对劲,至于那个林先生,我们就没见到过,对了,刘大哥,那个林先生叫什么?”
黄甜一个哆嗦:“疯子的名字有什么好问的……”
刘大哥道:“好像叫林……林宝……”
“林宝康!?”邵大力猛地站起来说道,他的脸色在瞬间变得煞白。
刘大哥道:“对对对,就叫林宝康!”
富文娜奇道:“邵大力,你怎么会知道?”
邵大力的两篇嘴唇都在颤抖:“天……天啊……胡哥……银子姐……他就是,他就是……”
胡知道说:“别激动,慢慢说,就是什么?”
邵大力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口喘气:“他……他就是何川!就是那天来的疯子啊!我……精神病院的人抓他回去的时候,就,就叫他林宝康!”
MY GOD! 29,幽灵
那个某天早上忽然在我们家门口出现,硬要认我们为结义兄嫂的疯子何川,居然就是卖房子给我们的孙小姐的未婚夫林宝康。
事情的复杂和蹊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之外!
如果林宝康的发疯源自明月小区,为何明月小区连死7人,独独是他一人疯癫而不致命呢?从时间上来推算,林宝康的发疯尚且在201研究生死亡之前,因为据后来了解,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住户基本上都知道林宝康发疯这件事,除了我们和5楼的5位大学生。
如果说林宝康的发疯源于明月小区,那么他疯癫后所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跟我们明月小区的凶险有直接联系呢,那张奇怪的照片他又是从哪里找来的?
我觉得一刻也不能等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段杏芳,把倪老伯的动向问清楚,或者,直接去精神病院探视林宝康。
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总应该能挖出点什么的!
我和胡知道决定明天去段杏芳的“猫王国”。
海洋和邵大力自告奋勇说去探视林宝康。
回头看王大哥没了声响,原来他已经醉了,趴在桌子上发出鼾声,眼角悬垂着一滴晶莹的泪水。
这泪水仿佛催化剂,更坚定了我们探明究竟的信念! 段杏芳的“猫王国”在郊区,我们到那的时候是早上九点多钟。我和胡知道都和单位请了假,扣钱也无所谓了,有些事情不弄清楚,憋在心里做什么事都是三心二意错误连连的。
一个单门独户的大院子,离老远我们就闻到浓烈的异味。到院子的大门口,我们已经被熏得脑袋发晕,记得上次来采访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臭,看来,段杏芳这里的流浪猫是不断增加啊。里面一片此起彼伏,让人胆战心惊的“喵喵”声。
还好人类的适应能力强,在一个环境中待时间长了,有了缓冲,就会对某种嗅觉听觉产生免疫。这不,在门口站了一分钟,我们已经渐渐回过神来。
段杏芳还记得我,一开门就说:“是雪记者啊,欢迎欢迎,你看看这里,也没有个落脚地方……”我朝院子里一看,心中不由又对段杏芳产生一丝同情,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爱猫的人士,养一两只猫可能会让你心情愉快,养十只猫就会让你手忙脚乱心情狂躁,100只呢,1000只呢?漫山遍野一样的猫向你扑过来,磨牙练爪,真的会连杀猫的心都有啊……
猫王国,名副其实,真是壮观得可以啊,黑压压全是猫咪,打架的,伸懒腰的,睡觉的,爬墙的,撕纸片的,咬拖鞋的……我的妈呀!如果不是天井的上方用网兜围住,恐怕还有“越狱”的,就算这样,头顶的网兜上也乱七八糟挂着十几只猫。
我说:“段姐,我们这次不是来采访的,就是想问你点事情。”
段杏芳说:“好啊,没问题,你们从后门进来吧,我后院隔开了,还算干净。”说着把前门关上,把我们从后面领进一个狭小的后院,段杏芳招呼我们在院子里的矮木凳上坐下,给我们一人拿了一瓶矿泉水,说,“我到卫生间冲个澡,换套衣服再来陪你们。”
段杏芳冲完澡出来后,胡知道同学眼睛猛地一亮。气得我偷偷拧了他一家伙。
换过衣服的段杏芳就像剥了皮的春笋一样,从脏兮兮的农妇样,一下子变得白嫩水灵,怪不得,怪不得她能把古董店老板唐毅松和馄饨店老板黄拐子迷得团团转。
她那副捏得出水来的笑脸,略带一丝被猫抓破的可怜血痕,简直就是天生尤物的招牌啊。
段杏芳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问:“雪记者,到底是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这位你同事?”
胡知道同学非常没出息地脸红起来,我说:“这是我老公,刚刚结婚没多久。”
段杏芳说:“那要恭喜啊。” 我说:“你肯定没想到,我们的新房在哪里?”
段杏芳眨眨眼,表示不明白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住的地方和你还很有渊源呢,我们的新房是明月小区的601室。”
段杏芳猛地打了个哆嗦,手上的毛巾飘落到地上。我和胡知道两双眼睛注视着她,段杏芳足足愣了有半分钟,这才回过神来,喃喃道:“怎么会是哪里,你们怎么住那里去了,我……我和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说:“我们是和孙小姐买的房子。”
段杏芳吃惊道:“孙敏把房子卖给你们了?……她为什么把房子卖了!她不是买来和宝康结婚的么?”
原来她也知道林宝康,我说:“林宝康疯了,有一阵子了。段姐,相信你也知道这栋房子的古怪,我们就是想弄明白到底古怪在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初的房主倪先生是怎么把楼卖给你的,他自己又跑到哪里去了?”
段杏芳的嘴唇瑟瑟发抖:“林宝康疯了,天,怎么会……倪先生,你……你们是说倪汉民?”
(倪老伯的名字叫倪汉民。)
我和胡知道点点头,胡知道说:“这栋楼死的第一个人是他的女儿倪燕,接触过这栋楼的人都知道,这楼的古怪多半和地基下的古墓女尸有关。要了解更详细的资料,恐怕只有找到倪老伯,他才是亲眼见过那个古墓的人。”
段杏芳忽然蹲下来捂着脸:“可不可以不要问我那里的事,我不想再和那栋楼有任何瓜葛,那,那里不是人能呆的地方……” “段姐,谁都不想碰上这些事情,可是,为这栋楼,已经有八个人死去,一个人发疯。”我把话往残忍里说,“你知不知道,这九个人或多或少与你有些关系,如果不是你把倪汉民的楼吃下来,再倒腾给别人,也许这栋楼到现在仍然没有住客,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段杏芳的眼泪流了下来:“九个……九个……已经有这么多人出事了么……”
我说:“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以为只要我自己摆脱阴楼,就不会再有事……为了忘掉那个地方,我才养猫,我问过城东的崔瞎子,说猫是驱邪的。”
我和胡知道一愣,驱邪?看来段杏芳在阴楼也“碰到”过骇人的事情。
胡知道眉头一皱,问:“驱什么邪?”
段杏芳连忙捂住嘴巴,好像害怕她说漏了嘴会被谁听到一样,猛劲摇头:“没,没……”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怎么能瞒得住我和胡知道,我朝胡知道使了个眼色,胡知道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茶叶的铁罐,打开盖子,倒出那枚玉蝉:“段大姐,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吧。”
段杏芳的嘴里像突然跳进了一只蛤蟆,牙齿得得地打着冷战:“这……这东西怎么会在……你们这里!?”
我说:“段姐,我们知道这东西是你借着给黄拐子送猫肉的机会包到猫肉馄饨里去的,对不对?”
段杏芳猛地跳了起来:“你们……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是什么?!”
我一愣,段杏芳吃惊之余,冒出一句“你们是什么”,她问的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人”,她以为我们是“什么”?
非人类?
我说:“段姐,我们当然是人。我们只是明月小区的普通住客,想弄明白明月小区不断出事的原因而已。”
段杏芳脸色稍稍平静:“你们不该追究的,你们应该搬出那个地方,再也别去想、别去管那个地方。”
我说:“段姐,逃避不是办法,更何况,我们逃避不起,你知道,工薪阶层嘛,哪能说换据点就换据点的。住在明月小区的,多半和我们是同一个阶层,他们也不会轻易搬出的,段姐,你难道愿意继续看到有人死亡吗?你知道最近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吗,她是用大门将自己夹死的。”
段杏芳的眼泪终于大颗大颗抛落下来:“怨我,都怨我……要不是我贪那个便宜……我……好吧,我原原本本说给你们听就是,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少耳目了,这种日子我也受够了……”
胡知道说:“耳目,谁的耳目?”
段杏芳道:“幽灵的耳目!”
我和胡知道目瞪口呆:“幽灵?!” 段杏芳说:“是的,幽灵,很多很多幽灵,有的躲在你梦里,有的躲在柜子里,有的躲在镜子里,他们最喜欢捉弄人,最喜欢吓人,你们不知道的,你们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胡知道说:“好吧,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幽灵?”
段杏芳说:“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处都是,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他们想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明明记得某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怎么去找也找不到,等过一阵不经意一瞥,那东西赫然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点点头,这情况太普遍了,尤其对我这个乱扔钥匙乱扔手机的马大哈来说。
胡知道问:“那么,你的意思是……”
段杏芳说:“没错,这就是幽灵在捣鬼,他们把东西用障眼法藏起来,让你急得团团转,你越是急他们就越是开心,所以,那些东西你越急越找不着,你要不急了,那些东西就自动出来了。”
我说:“幽灵到底是什么?”心说莫非就是鬼魂,阴楼的鬼魂的确不少,至少我们知道的就有七个,可是,在段杏芳拥有阴楼的那段时间,不应该有着么多的吧?
莫非,这阴楼之前还有不为人所知的历史?
段杏芳摇摇头,脸上现出那种迷惘的神色,良久开口道:“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在没养这些该死的猫之前,在没有买明月小区那个该死的房子之前,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正式的,有编制的那种。”
段杏芳为什么会知道这块地皮呢?那得要上溯到民国时期,段杏芳的祖辈,曾经显赫一时,是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堂兄弟,时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行长,是个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北洋军政府两边都能吃得开的人物。
苏州西中市区域仍旧保留有“老中国银行大楼”的民国建筑,而苏大附近的那片废墟原先也隶属中国银行,乃是其名下的职工宿舍。
(果然,在阴楼之前还有历史,听到这里我就在想,段杏芳所说的幽灵会不会是这个老建筑遗留下来的亡魂呢,这个老建筑当初有没有发生什么人间惨剧呢?)
当年那个职工宿舍落成后就怪事连连,好多人住在里面发了疯,搞得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住在那里,最后银行职员全部搬走,大楼就此废弃。然而那年头有很多难民和生意人蛮不畏死,大楼遂变成难民营。
又过了几年,住在里面的难民也因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可怖事情搬了出去,最后整栋楼里只住着一户生意人。
那个生意人是在养育巷开照相馆的田福生。
(我和胡知道听段杏芳讲到这里,差一点跳将起来,田福生,不就是那个疯子何川嘴里的田蟑螂么!如果何川是孙小姐的丈夫林宝康,是个现代人,他又怎么知道民国年间的田蟑螂!怪!怪!怪!怪得离谱!)
田福生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父子两个人在那栋楼里住了好多年,后来日本人轰炸苏州,一颗炸弹掉下来,炸掉了那栋大楼。日本人的飞机走后,大家在废墟里只挖出了田福生,却没有找到他儿子的尸体,这也是当年的一大怪事。
田福生死后,他在养育巷的那个照相馆也不见有人去接手,后来就被警察局封了。
因为这段轶事,大家都对那块地方敬而远之,连新中国成立以后,那地方也好像被刻意从市区地图上抹掉,没有人愿意在那多费精力。但是段杏芳心想,这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那栋楼被炸掉的地方荒草弥漫,每日阳光照射,怎么说也不会再有问题。就鼓动倪汉民联合几个拆迁户把那地皮给要了下来。
明月小区开始动工的时候,段杏芳为了避嫌,并没有去工地看过。倪汉民亲眼目睹从地基里挖出古墓,他害怕段杏芳担心,也没有将这事告诉段杏芳。
倪汉民并不知道那段民国轶事,当然也没有足够的警觉心。
等到房子盖好,倪燕出了事,倪汉民的心中才恐慌痛苦起来。他这才跑去和段杏芳汇合,把建房时发生的怪事详详细细和段杏芳说了一遍。
那段杏芳也是十分慌张,又把那段民国轶事给倪汉民从头到尾细说一番。 倪汉民听完段杏芳的故事,嘴里不停喃喃念叨:“田福生……田福生……”
段杏芳说:“汉民哥,你可是想起什么来了?”
倪汉民三下五除二把自己的上衣给扯了下来,精赤着上身。段杏芳满面红晕,心说,怎么谈着正事呢,他就猴急着要来这个……
哪知倪汉民脱衣并非为了段杏芳所想的那事,只见他慢慢转过身去,段杏芳一下子瞪大眼睛!
就见在倪汉民的背上,写着好大一个“田”字!那“田”字从肩胛到腰眼,布满了整个背部,细看之下,那又不是写出来的,就像平白无故隆起的血色伤痕。
段杏芳说:“这……这是怎么了?”
倪汉民摇头:“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天每天起床背都痒,使劲挠,就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田’字吧,恐怕……恐怕和你说的那个田福生有关。”
段杏芳说:“可是田福生已经死了啊。”
倪汉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下落不明,他们父子俩敢住在那楼里十几年,肯定和这鬼相熟!”倪汉民说着说着眼睛里都快滴出血来,“她害死倪燕,我总得要知道为什么!……那个什么田福生的儿子一定有办法和那女鬼联系……不对,不对,是这鬼也要和田福生的儿子联系,要不她干嘛在我背上写这个鬼‘田’字!”
段杏芳看倪汉民势如疯狂,也不知如何解劝,倪汉民说:“小芳,你现在总共有多少钱?”
段杏芳说:“不到五万块。”
倪汉民说:“你把这五万块给我,我把明月小区顶给你,我一定要找到田福生的儿子!”
段杏芳很是心动,最后还是把5万元私房钱交给了倪汉民,然后两个人跑去办了房产交割。明月小区从那个时候起,就变成了段杏芳的。
一个单身女子,住进空荡荡的大楼,大楼地基里有具古代女尸,而且这个大楼楼顶还刚刚莫名其妙摔死过一个女子,想不去害怕想不去胡思乱想都难。
段杏芳整夜整夜开着电灯,即便是开灯睡觉,还是噩梦连连。非但是噩梦连连,屋子里几乎天天都有怪事发生,晚上段杏芳脱在房门口的鞋子,第二天一准不见,找来找去,不是在一楼找到就是在二楼找到,当时那两层房子还只是粗毛胚结构,连房门也没有。段杏芳疑心是谁和她开玩笑,想来想去又想不出能和她开这种玩笑的人选。
没过几天,就有了神经衰弱的迹象。
房子太毛胚了,一时半会也租不出去,段杏芳一边寻找工作,一边就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是卖是租都行。
每天晚上,段杏芳都不愿意靠近那个房子,尽量在外面胡混。因为身上钱不多,也不能去什么娱乐场所,跑来跑去就是几个街心公园,再不就是溜溜步行街。
段杏芳和黄拐子就是在观前步行街的休息长椅上认识的。
一个心怀胆怯,想找个依靠,一个存心勾搭。
两个人很容易便混在了一起。
有黄拐子作伴,段杏芳才有回明月小区的胆子。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黄拐子天天晚上陪段杏芳回家,第二天一早才离开。
黄拐子在明月小区住了大概半个月,就再也撑不下去了。
因为,怪事已经在他们身上发生。 明月小区的房子因为实在便宜,经过那家无良的中介公司一宣传,果然有卖有租,段杏芳的手头倒是慢慢松了起来。就是在那一阵,段杏芳四处闲逛,在古玩城买一个“猫戏图”古瓷片时,认识了唐毅松。
唐毅松一勾搭,寂寞难耐心理空虚的段杏芳就上了钩,唐毅松见识了段杏芳左边胸脯上纹的桃花,知道了段杏芳的艳名叫小桃红,他自然也看到了段杏芳右边胸脯上的大痣。
当时,唐毅松还曾拿看古董的放大镜仔细看过那颗痣,他说小桃红的那颗痣里面黑斑涌动,似乎有个什么图案。段杏芳连骂他色情,掩住了胸脯,但是从唐毅松那里离开后,她却静不下心来。
唐毅松的那句话,她还是信的。
她直接去了一家美容医院。要求医生帮她除掉这个痣,但是必须保证这个痣除下来还是完整的。
美容医院是私营的,那个主刀医生没有问她为什么不用电炙法除痣,反而选择痛苦地挨刀。顾客就是上帝,能做多收钱的项目就不做少收钱的,医生乐得其所。
痣很顺利地除了下来,段杏芳问医生要了显微镜下的玻璃夹片,将那痣夹着,要求医生陪她去“看一看”这颗痣。
那医生头一次遇到这种嗜好的顾客,只当段杏芳是变态。但变态的钱也是钱,段杏芳塞给他两百块钱,那医生毫不犹豫地将一架显微镜扛到了段杏芳所在的病房。
通过显微镜,可以清晰地看到,痣里面的黑斑形成的是一个蝉的图案,毫无疑问,那是蝉的图案,而且是蝉腹那一面的图案。
段杏芳感觉不到“涌动”,也不知是不是这颗痣脱离了身体,就“死亡”了呢?难道说唐毅松看到的,竟是这蝉斑在爬动?
那医生看段杏芳凑在显微镜跟前久久不动弹,害怕出什么问题,便用手推了一推。哪知段杏芳正沉浸在恐惧中,被医生这么一推,陡然尖叫起来,把那医生吓得一下子仰跌过去,撞翻了一个吊水用的挂架。 那医生姓田,性格还算蛮好,不怒反笑:“怎么了?显微镜里还能看到史蒂芬·金?”
段杏芳结结巴巴说:“我的痣里面……好像有只‘知了’……”
田医生一愣,走上去,段杏芳让到一边,田医生盯着显微镜看了很久,段杏芳感觉脚都站麻了,田医生才抬起头来,盯着段杏芳缓缓说道:“你知道幽灵吗?”
段杏芳摇摇头,田医生走过去关上病床门,示意段杏芳坐在床上,他很是兴奋地侃侃而谈:“你知道吗,我以前喜欢收集古籍,在一个旧书店买过一本很古老的线装书,那上面说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化成魂凝成魄,而冤死之人就没那么简单,他们在死之前会有一股无法解脱的执念,这股执念会变成幽灵附属在冤魂之上,幽灵因为只是单独的执念,所以它可以演化的相态取决于执念的内容,它附属于冤魂却又不受冤魂控制。如果幽灵撞见和这执念相关的物事,都会在其身上留下烙印,烙印的方式有很多种。”
(晕,原来幽灵是这个东西,到有些类似日本人说的‘怨念’,这理论真强大~)
段杏芳头皮发麻:“你说这个痣……是幽灵的烙印?”
田医生嘿嘿一笑:“那书上说,痣也是烙印的一种。所以说幽灵无处不在,有多少人会去留意自己身上的大痣呢?你这个痣里面的行走像蝉,证明这股执念和蝉有关,你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和蝉有关的事情……”
田医生口若悬河口沫横飞,段杏芳却越听越心惊,连带看这个医生都觉得很恐怖,她强自压住心中的恐惧,平静地骂了一句“胡说八道”,“若无其事”地走出医院。
一出美容医院的大门,便落荒而逃回了家。
到家翻出那枚玉蝉,左思右想,总觉得一系列厄运和这玉蝉大有关联,要不怎么痣里也有蝉的图案呢。这玉蝉一定是不洁之物,她决定甩开玉蝉,把厄运转嫁给别人。
所以,她去了黄拐子的猫肉馄饨店,悄悄把玉蝉和在馅料了包了个馄饨。
事情就是这么巧,这玉蝉竟然又被她新认识的姘头唐毅松得了去。 段杏芳的故事迂回曲折,骇人听闻。那个神秘的田医生,怎么会那么清楚什么幽灵的事情,难道真如他自己说的,都是从古籍上看来的?
从古籍上看来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认真地跟段杏芳讲述。
听起来,好像这个医生倒是小题大做,故事把话题往“蝉”上面带?
段杏芳被吓坏了胆子,这些东西她应该都没有细细分析过,我心说,这个田医生,十分有见面的价值!
在回来的路上,胡知道说:“银子,你说段杏芳嘴里的田医生,会不会是那田福生的什么人?他们可都是姓田啊。”
我心中也是那么怀疑的,我说:“那家美容整形医院我知道,咱们中午和邵大力他们碰个头,下午就去那医院找一下田医生。”
胡知道说:“知道了,也是,现在猜什么也是白猜。”
找了家饭馆,刚刚坐下来,邵大力的电话也就打了过来,我说:“怎么样,见到林宝康没?”
邵大力说:“一言难尽,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说了饭馆的位置,邵大力他们现在的位置离我们这里并不太远,我说正好,一起来吃个饭,下午我们一起去个地方,见个人。
不到一刻钟,邵大力和海洋就来到饭馆。两个人满头大汗,坐下来猛喝两口水,邵大力说:“胡哥,银子姐,你们知道吧,原来林宝康已经死了。”
我和胡知道一怔:“死了?”
海洋接口说:“医院里说,林宝康一个礼拜前就死了,说是什么精神恍惚,从安全通道的楼梯上滚下去死的,七楼滚到二楼,医院还赔了林家一笔钱,所以我们问到林宝康,医院里的人都没有好脸色。”
还是海洋说话比较有条理,我们总算听清楚了,失足从楼梯上摔下,这种死法还不算怪异,我现在最怕听到和阴楼有关的死亡事情,但愿林宝康的死是个纯粹的意外。
邵大力说:“我们问明白了林家的住址,原来就在本市北郊渭塘镇的一个什么村,我和海洋一合计,反正闲着也闲着,不如去林家看看,说不准有什么发现呢?”
我问:“那有没有什么发现?”
邵大力说:“有,那当然有,海洋,把东西拿出来!”
海洋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纸片,那是一张老照片。
照片是旧社会那种全家福,有穿长褂子留胡子的老头,也有坐在木头摇椅上的老太太,还有一堆憨头憨脑的青年男女。我问:“这是什么?”
海阳说:“这是林家祖上的老照片,银子姐,你看看背面。”
我把照片掉了个面,眼前不由一亮,只见右下角依稀有行不清不楚的繁体印章字:福生田记照相馆。
天,竟然是在田福生的照相馆照的。如此看来,田宝康知道田福生这个人就不奇怪了,他祖上一定有人和田福生认识。
可是,当初他带过来的,有着我和胡知道的老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那张照片也是福生田记照相馆出品?我将这个疑问提了出来。
邵大力笑道:“你们要是知道林宝康是干什么的,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胡知道说:“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邵大力说:“他是海报设计师,算得上半个艺术家呢。”
我们恍然大悟,海报设计师,一般来说都是PS高手,熟练试用phothoshop,谁都能造出一张老照片来,更何况,林宝康还有老照片可以参照。
我们只是不明白,他跑到601来的目的何在?
可是,要想弄明白疯子的目的,除非我们也是疯子!
“还有哦。”邵大力说着又献宝似的拿出一卷纸。
胡知道好奇地问:“这又是什么东西。”
海洋说:“一幅画,林宝康死之前一直在画这幅画,这是医院方面告诉林家人的,这幅画也被当成重要遗物送到林家。”
画是用铅笔画的,一张人物肖像。准确地说,是一张古装人物肖像,头戴文生公子巾,面容俊朗,双眉似剑,下巴很有棱角,没有文生的那种文弱书生气,倒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剑客。
我说:“林宝康死之前画这个是什么意思?”
邵大力道:“那哪里知道,他那会精神还是不正常的,也许我们梦里见过那个吓人的古装女子,他老人家梦里就见过这个家伙呢,嘿嘿……”
我们无语,胡知道让海洋先把画收起来,说道:“你们是怎么骗来这画的?”
邵大力又是嘿嘿一笑,洋洋得意地说:“我说我们是孙小姐的朋友,代孙敏来看看林宝康,谁知道林家人深信不疑,还差点留我们吃饭呢,要张照片要张画那有什么稀奇。”
海洋掐了他一下,说:“胡大哥,银子姐,你们在段杏芳哪里打听到了什么没有?”
说话间,菜和饭都陆续端了上来,我们边吃边说,把从段杏芳那里得来的讯息和我们推论一一明细。
邵大力听到吃惊之处,好几次把饭呛入气管,从鼻孔里喷出米粒来。
唉,真是让人大倒胃口。 “怎么,你们不信?”那女人低下头,拆下盘头,撩开头发说,“你们看看。”
这时正好轮船上的探照灯光扫到她们身边,就听众位贵妇齐齐发出一声惊呼,连那个哭泣的女人也不例外。田顺来虽然离得比较远,但少年人眼力尖,也瞥见那女人的发间头皮上,沟壑纵横,尽是刀疤。
刀疤处没有毛囊,所以那女人的头发披散下来看起来一络一络的泾渭分明,很是可怕。
旁边一个女人问:“雅梅,这……这是怎么来的?”
叫雅梅的女人慢慢把头发重新盘起,微微一笑说:“被人砍的,被一个疯子砍的。”
四周的女人们都惊叫起来,那个雅梅的女人满脸得色地说道:“你们都想像不出来吧,好了好了,我就不卖这个关子了,听口音你们该能分辨出来,我是湖南常德人,老实说,我的出身并不好,山村旮旯里的。我出生刚刚六个月的时候,家人在下地干活,就把我放在摇篮里,把摇篮搁在地头山路上,山里人都这么照顾孩子。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个疯子,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伙都叫他的外号——邋遢书生,听说还是个清末老秀才。那天,那个老东西不知为什么原因,举着一把菜刀,冲过来对着摇篮里的我就砍。”
四周的阔太太们都惊呼地捂着脸,田顺来心说,六个月大的孩子,那还不是一刀了结,这女人也太夸张了,不由自主,又靠近几步。那女人接着说:“这老东西足足砍了我二十六刀,我流出来的血把整个摇篮都染红了,地里干活的父母大惊,急忙跑过来,钉耙锄头地赶走了疯子,可是已经晚了,眼见我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连哭声都彻底熄灭了。”
大伙听得大气不敢喘一口,四周只听到江浪拍击船身的声音,雅梅从旗袍衣襟里掏出一方丝巾,执起一端擦了擦湿润的眼角,说:“那时,父母只当我已经死了,果然,到了家里,就断了气。一家人极度伤心,我奶奶却说了句,反正是个女娃,死了也就死了,埋了算。我爷爷当即就煽了奶奶一个巴掌,奶奶不啃声了,赌气回了屋内。我爸妈和我爷爷想想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最后还是扛上锄头去了山腰,刨了个坑,就准备把我埋掉。”
“坑刨好了,妈妈把我放进去,父亲给我填土,几锹土落到身上,爷爷忽然叫了起来,他说看到我的一根手指动了一下。我父母都劝他,说怎么可能还能动弹,肯定是泥土打在手指上闹出的动静。可我爷爷不依,仍旧把我捞了上来,说死马也得当活马医一下才知道,何况是个孩子。爷爷把我抱了回去,找了黑沟泥给我糊满全身,用我们那里的土办法给我处理伤口,屋顶上晒的草药是现成的,草药熬了一锅米汤,从我牙缝里灌进去,给我提神吊命,忙活到半夜,一直抱在爷爷手里的我身子陡然蜷缩了一下,发出一声咳嗽,我这就算二次活过命来。” 田顺来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就在这时候,江面上忽然刮起风来,伴着风来的便是浪,浪打得船身前后左右摇晃,甲板上不再似先前那般平稳。那几个阔太太大惊失色,扶着栏杆尖叫。有几个船员过来扶着她们进舱室,田顺来少年人好奇,故事听到一半哪里肯罢休,想这几个女人回到舱室多半还要接着讲,便大了胆子尾随她们进入贵宾船舱。那几个船员只当田顺来是某个太太道跟班,倒也没有在意他。
甲板上的建筑总共有两层,下层有半数面积是个大的休息厅,里面有留声机放音乐,还有好些桌子座位用来休息喝酒打麻将。休息室里虽说也摇摇晃晃,但一来有座位依靠,而来不用直接面对大风大浪,感觉上要好得多。
那几个太太果然围着一张麻将方桌边打牌边唠嗑,只是那个刚刚死了丈夫的明兰好像没了打牌的兴致,把座位让给了别人,她坐到雅梅的身旁,低着头。继续听雅梅把她的经历断断续续讲出来。
田顺来大着胆子,有模有样翘着二郎腿坐在她们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幸亏应付风浪,船上的工作人员都跑甲板上去帮手了,倒也没侍者来赶他。田顺来竖起耳朵,只听那雅梅继续说道:“你们问什么?那是什么男人?哈哈,我告诉你们,我救起来的男人可不是别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啊。”
肖太太说:“不会吧,雅梅你救了他,他就对你以身相许,怎么听着像张恨水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不信是不是?”雅梅在肖太太胳膊上拧了一把,“不信你下次亲自问我老公去。”
肖太太说:“呦呦呦,你个小浪蹄子,不怕我抢了你的老公?”
看来这个肖太太和雅梅相当熟,雅梅嘻嘻直笑:“你去抢啊,不去不是人。”
一群女人都放浪形骸地笑了起来,其他女人跟雅梅不是很熟,都和肖太太打听:“雅梅先生是什么来头啊?”
肖太太说:“雅梅福气好,他先生是戴老板,全中国最大的湘绸商人,绸布都卖到军队里去了。”
一行人啧啧赞叹,田顺来没听说过戴老板这个人,但看众位太太一脸羡慕的表情,显然这个戴老板是位豪富。
胡知道说:“这孙小姐和林先生到底怎么了?”
刘大哥道:“他们也不容易,都是这个城市的外来客,在这里打拼,好不容易在段杏芳手里盘下这个房子,装修了准备结婚,可哪里想到,林先生不知怎么地,居然神经出了毛病,发了疯,谁都不认得了。孙小姐一开始整天以泪洗面的,说是自己买了这个不吉利的房子,害得林先生出了问题,后来我老婆常常去劝劝她,她就也不怎么闹了。书读得多的人,脑子还是蛮通透的,她说要把房子再卖掉,免得什么……睹物思人……说要把卖房子的钱全部给林先生家里,她要离开苏州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回来。”
我说:“那个林先生为什么发疯呢?”
刘大哥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记得他们小两口头天晚上还在我摊子上吃过麻辣烫,第二天就传出林先生疯了的消息。”
周立立说:“胡哥,银子姐,你们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也刚刚住进来没几天,那个孙小姐倒是见过几面,也没看出来神色有什么不对劲,至于那个林先生,我们就没见到过,对了,刘大哥,那个林先生叫什么?”
黄甜一个哆嗦:“疯子的名字有什么好问的……”
刘大哥道:“好像叫林……林宝……”
“林宝康!?”邵大力猛地站起来说道,他的脸色在瞬间变得煞白。
刘大哥道:“对对对,就叫林宝康!”
富文娜奇道:“邵大力,你怎么会知道?”
邵大力的两篇嘴唇都在颤抖:“天……天啊……胡哥……银子姐……他就是,他就是……”
胡知道说:“别激动,慢慢说,就是什么?”
邵大力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口喘气:“他……他就是何川!就是那天来的疯子啊!我……精神病院的人抓他回去的时候,就,就叫他林宝康!”
MY GOD! 29,幽灵
那个某天早上忽然在我们家门口出现,硬要认我们为结义兄嫂的疯子何川,居然就是卖房子给我们的孙小姐的未婚夫林宝康。
事情的复杂和蹊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之外!
如果林宝康的发疯源自明月小区,为何明月小区连死7人,独独是他一人疯癫而不致命呢?从时间上来推算,林宝康的发疯尚且在201研究生死亡之前,因为据后来了解,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住户基本上都知道林宝康发疯这件事,除了我们和5楼的5位大学生。
如果说林宝康的发疯源于明月小区,那么他疯癫后所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跟我们明月小区的凶险有直接联系呢,那张奇怪的照片他又是从哪里找来的?
我觉得一刻也不能等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段杏芳,把倪老伯的动向问清楚,或者,直接去精神病院探视林宝康。
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总应该能挖出点什么的!
我和胡知道决定明天去段杏芳的“猫王国”。
海洋和邵大力自告奋勇说去探视林宝康。
回头看王大哥没了声响,原来他已经醉了,趴在桌子上发出鼾声,眼角悬垂着一滴晶莹的泪水。
这泪水仿佛催化剂,更坚定了我们探明究竟的信念! 段杏芳的“猫王国”在郊区,我们到那的时候是早上九点多钟。我和胡知道都和单位请了假,扣钱也无所谓了,有些事情不弄清楚,憋在心里做什么事都是三心二意错误连连的。
一个单门独户的大院子,离老远我们就闻到浓烈的异味。到院子的大门口,我们已经被熏得脑袋发晕,记得上次来采访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臭,看来,段杏芳这里的流浪猫是不断增加啊。里面一片此起彼伏,让人胆战心惊的“喵喵”声。
还好人类的适应能力强,在一个环境中待时间长了,有了缓冲,就会对某种嗅觉听觉产生免疫。这不,在门口站了一分钟,我们已经渐渐回过神来。
段杏芳还记得我,一开门就说:“是雪记者啊,欢迎欢迎,你看看这里,也没有个落脚地方……”我朝院子里一看,心中不由又对段杏芳产生一丝同情,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爱猫的人士,养一两只猫可能会让你心情愉快,养十只猫就会让你手忙脚乱心情狂躁,100只呢,1000只呢?漫山遍野一样的猫向你扑过来,磨牙练爪,真的会连杀猫的心都有啊……
猫王国,名副其实,真是壮观得可以啊,黑压压全是猫咪,打架的,伸懒腰的,睡觉的,爬墙的,撕纸片的,咬拖鞋的……我的妈呀!如果不是天井的上方用网兜围住,恐怕还有“越狱”的,就算这样,头顶的网兜上也乱七八糟挂着十几只猫。
我说:“段姐,我们这次不是来采访的,就是想问你点事情。”
段杏芳说:“好啊,没问题,你们从后门进来吧,我后院隔开了,还算干净。”说着把前门关上,把我们从后面领进一个狭小的后院,段杏芳招呼我们在院子里的矮木凳上坐下,给我们一人拿了一瓶矿泉水,说,“我到卫生间冲个澡,换套衣服再来陪你们。”
段杏芳冲完澡出来后,胡知道同学眼睛猛地一亮。气得我偷偷拧了他一家伙。
换过衣服的段杏芳就像剥了皮的春笋一样,从脏兮兮的农妇样,一下子变得白嫩水灵,怪不得,怪不得她能把古董店老板唐毅松和馄饨店老板黄拐子迷得团团转。
她那副捏得出水来的笑脸,略带一丝被猫抓破的可怜血痕,简直就是天生尤物的招牌啊。
段杏芳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问:“雪记者,到底是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这位你同事?”
胡知道同学非常没出息地脸红起来,我说:“这是我老公,刚刚结婚没多久。”
段杏芳说:“那要恭喜啊。” 我说:“你肯定没想到,我们的新房在哪里?”
段杏芳眨眨眼,表示不明白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住的地方和你还很有渊源呢,我们的新房是明月小区的601室。”
段杏芳猛地打了个哆嗦,手上的毛巾飘落到地上。我和胡知道两双眼睛注视着她,段杏芳足足愣了有半分钟,这才回过神来,喃喃道:“怎么会是哪里,你们怎么住那里去了,我……我和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说:“我们是和孙小姐买的房子。”
段杏芳吃惊道:“孙敏把房子卖给你们了?……她为什么把房子卖了!她不是买来和宝康结婚的么?”
原来她也知道林宝康,我说:“林宝康疯了,有一阵子了。段姐,相信你也知道这栋房子的古怪,我们就是想弄明白到底古怪在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初的房主倪先生是怎么把楼卖给你的,他自己又跑到哪里去了?”
段杏芳的嘴唇瑟瑟发抖:“林宝康疯了,天,怎么会……倪先生,你……你们是说倪汉民?”
(倪老伯的名字叫倪汉民。)
我和胡知道点点头,胡知道说:“这栋楼死的第一个人是他的女儿倪燕,接触过这栋楼的人都知道,这楼的古怪多半和地基下的古墓女尸有关。要了解更详细的资料,恐怕只有找到倪老伯,他才是亲眼见过那个古墓的人。”
段杏芳忽然蹲下来捂着脸:“可不可以不要问我那里的事,我不想再和那栋楼有任何瓜葛,那,那里不是人能呆的地方……” “段姐,谁都不想碰上这些事情,可是,为这栋楼,已经有八个人死去,一个人发疯。”我把话往残忍里说,“你知不知道,这九个人或多或少与你有些关系,如果不是你把倪汉民的楼吃下来,再倒腾给别人,也许这栋楼到现在仍然没有住客,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段杏芳的眼泪流了下来:“九个……九个……已经有这么多人出事了么……”
我说:“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以为只要我自己摆脱阴楼,就不会再有事……为了忘掉那个地方,我才养猫,我问过城东的崔瞎子,说猫是驱邪的。”
我和胡知道一愣,驱邪?看来段杏芳在阴楼也“碰到”过骇人的事情。
胡知道眉头一皱,问:“驱什么邪?”
段杏芳连忙捂住嘴巴,好像害怕她说漏了嘴会被谁听到一样,猛劲摇头:“没,没……”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怎么能瞒得住我和胡知道,我朝胡知道使了个眼色,胡知道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茶叶的铁罐,打开盖子,倒出那枚玉蝉:“段大姐,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吧。”
段杏芳的嘴里像突然跳进了一只蛤蟆,牙齿得得地打着冷战:“这……这东西怎么会在……你们这里!?”
我说:“段姐,我们知道这东西是你借着给黄拐子送猫肉的机会包到猫肉馄饨里去的,对不对?”
段杏芳猛地跳了起来:“你们……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是什么?!”
我一愣,段杏芳吃惊之余,冒出一句“你们是什么”,她问的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人”,她以为我们是“什么”?
非人类?
我说:“段姐,我们当然是人。我们只是明月小区的普通住客,想弄明白明月小区不断出事的原因而已。”
段杏芳脸色稍稍平静:“你们不该追究的,你们应该搬出那个地方,再也别去想、别去管那个地方。”
我说:“段姐,逃避不是办法,更何况,我们逃避不起,你知道,工薪阶层嘛,哪能说换据点就换据点的。住在明月小区的,多半和我们是同一个阶层,他们也不会轻易搬出的,段姐,你难道愿意继续看到有人死亡吗?你知道最近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吗,她是用大门将自己夹死的。”
段杏芳的眼泪终于大颗大颗抛落下来:“怨我,都怨我……要不是我贪那个便宜……我……好吧,我原原本本说给你们听就是,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少耳目了,这种日子我也受够了……”
胡知道说:“耳目,谁的耳目?”
段杏芳道:“幽灵的耳目!”
我和胡知道目瞪口呆:“幽灵?!” 段杏芳说:“是的,幽灵,很多很多幽灵,有的躲在你梦里,有的躲在柜子里,有的躲在镜子里,他们最喜欢捉弄人,最喜欢吓人,你们不知道的,你们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胡知道说:“好吧,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幽灵?”
段杏芳说:“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处都是,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他们想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明明记得某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怎么去找也找不到,等过一阵不经意一瞥,那东西赫然还在原来的地方……”
我点点头,这情况太普遍了,尤其对我这个乱扔钥匙乱扔手机的马大哈来说。
胡知道问:“那么,你的意思是……”
段杏芳说:“没错,这就是幽灵在捣鬼,他们把东西用障眼法藏起来,让你急得团团转,你越是急他们就越是开心,所以,那些东西你越急越找不着,你要不急了,那些东西就自动出来了。”
我说:“幽灵到底是什么?”心说莫非就是鬼魂,阴楼的鬼魂的确不少,至少我们知道的就有七个,可是,在段杏芳拥有阴楼的那段时间,不应该有着么多的吧?
莫非,这阴楼之前还有不为人所知的历史?
段杏芳摇摇头,脸上现出那种迷惘的神色,良久开口道:“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在没养这些该死的猫之前,在没有买明月小区那个该死的房子之前,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正式的,有编制的那种。”
段杏芳为什么会知道这块地皮呢?那得要上溯到民国时期,段杏芳的祖辈,曾经显赫一时,是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堂兄弟,时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行长,是个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北洋军政府两边都能吃得开的人物。
苏州西中市区域仍旧保留有“老中国银行大楼”的民国建筑,而苏大附近的那片废墟原先也隶属中国银行,乃是其名下的职工宿舍。
(果然,在阴楼之前还有历史,听到这里我就在想,段杏芳所说的幽灵会不会是这个老建筑遗留下来的亡魂呢,这个老建筑当初有没有发生什么人间惨剧呢?)
当年那个职工宿舍落成后就怪事连连,好多人住在里面发了疯,搞得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住在那里,最后银行职员全部搬走,大楼就此废弃。然而那年头有很多难民和生意人蛮不畏死,大楼遂变成难民营。
又过了几年,住在里面的难民也因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可怖事情搬了出去,最后整栋楼里只住着一户生意人。
那个生意人是在养育巷开照相馆的田福生。
(我和胡知道听段杏芳讲到这里,差一点跳将起来,田福生,不就是那个疯子何川嘴里的田蟑螂么!如果何川是孙小姐的丈夫林宝康,是个现代人,他又怎么知道民国年间的田蟑螂!怪!怪!怪!怪得离谱!)
田福生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父子两个人在那栋楼里住了好多年,后来日本人轰炸苏州,一颗炸弹掉下来,炸掉了那栋大楼。日本人的飞机走后,大家在废墟里只挖出了田福生,却没有找到他儿子的尸体,这也是当年的一大怪事。
田福生死后,他在养育巷的那个照相馆也不见有人去接手,后来就被警察局封了。
因为这段轶事,大家都对那块地方敬而远之,连新中国成立以后,那地方也好像被刻意从市区地图上抹掉,没有人愿意在那多费精力。但是段杏芳心想,这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那栋楼被炸掉的地方荒草弥漫,每日阳光照射,怎么说也不会再有问题。就鼓动倪汉民联合几个拆迁户把那地皮给要了下来。
明月小区开始动工的时候,段杏芳为了避嫌,并没有去工地看过。倪汉民亲眼目睹从地基里挖出古墓,他害怕段杏芳担心,也没有将这事告诉段杏芳。
倪汉民并不知道那段民国轶事,当然也没有足够的警觉心。
等到房子盖好,倪燕出了事,倪汉民的心中才恐慌痛苦起来。他这才跑去和段杏芳汇合,把建房时发生的怪事详详细细和段杏芳说了一遍。
那段杏芳也是十分慌张,又把那段民国轶事给倪汉民从头到尾细说一番。 倪汉民听完段杏芳的故事,嘴里不停喃喃念叨:“田福生……田福生……”
段杏芳说:“汉民哥,你可是想起什么来了?”
倪汉民三下五除二把自己的上衣给扯了下来,精赤着上身。段杏芳满面红晕,心说,怎么谈着正事呢,他就猴急着要来这个……
哪知倪汉民脱衣并非为了段杏芳所想的那事,只见他慢慢转过身去,段杏芳一下子瞪大眼睛!
就见在倪汉民的背上,写着好大一个“田”字!那“田”字从肩胛到腰眼,布满了整个背部,细看之下,那又不是写出来的,就像平白无故隆起的血色伤痕。
段杏芳说:“这……这是怎么了?”
倪汉民摇头:“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天每天起床背都痒,使劲挠,就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田’字吧,恐怕……恐怕和你说的那个田福生有关。”
段杏芳说:“可是田福生已经死了啊。”
倪汉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下落不明,他们父子俩敢住在那楼里十几年,肯定和这鬼相熟!”倪汉民说着说着眼睛里都快滴出血来,“她害死倪燕,我总得要知道为什么!……那个什么田福生的儿子一定有办法和那女鬼联系……不对,不对,是这鬼也要和田福生的儿子联系,要不她干嘛在我背上写这个鬼‘田’字!”
段杏芳看倪汉民势如疯狂,也不知如何解劝,倪汉民说:“小芳,你现在总共有多少钱?”
段杏芳说:“不到五万块。”
倪汉民说:“你把这五万块给我,我把明月小区顶给你,我一定要找到田福生的儿子!”
段杏芳很是心动,最后还是把5万元私房钱交给了倪汉民,然后两个人跑去办了房产交割。明月小区从那个时候起,就变成了段杏芳的。
一个单身女子,住进空荡荡的大楼,大楼地基里有具古代女尸,而且这个大楼楼顶还刚刚莫名其妙摔死过一个女子,想不去害怕想不去胡思乱想都难。
段杏芳整夜整夜开着电灯,即便是开灯睡觉,还是噩梦连连。非但是噩梦连连,屋子里几乎天天都有怪事发生,晚上段杏芳脱在房门口的鞋子,第二天一准不见,找来找去,不是在一楼找到就是在二楼找到,当时那两层房子还只是粗毛胚结构,连房门也没有。段杏芳疑心是谁和她开玩笑,想来想去又想不出能和她开这种玩笑的人选。
没过几天,就有了神经衰弱的迹象。
房子太毛胚了,一时半会也租不出去,段杏芳一边寻找工作,一边就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是卖是租都行。
每天晚上,段杏芳都不愿意靠近那个房子,尽量在外面胡混。因为身上钱不多,也不能去什么娱乐场所,跑来跑去就是几个街心公园,再不就是溜溜步行街。
段杏芳和黄拐子就是在观前步行街的休息长椅上认识的。
一个心怀胆怯,想找个依靠,一个存心勾搭。
两个人很容易便混在了一起。
有黄拐子作伴,段杏芳才有回明月小区的胆子。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黄拐子天天晚上陪段杏芳回家,第二天一早才离开。
黄拐子在明月小区住了大概半个月,就再也撑不下去了。
因为,怪事已经在他们身上发生。 明月小区的房子因为实在便宜,经过那家无良的中介公司一宣传,果然有卖有租,段杏芳的手头倒是慢慢松了起来。就是在那一阵,段杏芳四处闲逛,在古玩城买一个“猫戏图”古瓷片时,认识了唐毅松。
唐毅松一勾搭,寂寞难耐心理空虚的段杏芳就上了钩,唐毅松见识了段杏芳左边胸脯上纹的桃花,知道了段杏芳的艳名叫小桃红,他自然也看到了段杏芳右边胸脯上的大痣。
当时,唐毅松还曾拿看古董的放大镜仔细看过那颗痣,他说小桃红的那颗痣里面黑斑涌动,似乎有个什么图案。段杏芳连骂他色情,掩住了胸脯,但是从唐毅松那里离开后,她却静不下心来。
唐毅松的那句话,她还是信的。
她直接去了一家美容医院。要求医生帮她除掉这个痣,但是必须保证这个痣除下来还是完整的。
美容医院是私营的,那个主刀医生没有问她为什么不用电炙法除痣,反而选择痛苦地挨刀。顾客就是上帝,能做多收钱的项目就不做少收钱的,医生乐得其所。
痣很顺利地除了下来,段杏芳问医生要了显微镜下的玻璃夹片,将那痣夹着,要求医生陪她去“看一看”这颗痣。
那医生头一次遇到这种嗜好的顾客,只当段杏芳是变态。但变态的钱也是钱,段杏芳塞给他两百块钱,那医生毫不犹豫地将一架显微镜扛到了段杏芳所在的病房。
通过显微镜,可以清晰地看到,痣里面的黑斑形成的是一个蝉的图案,毫无疑问,那是蝉的图案,而且是蝉腹那一面的图案。
段杏芳感觉不到“涌动”,也不知是不是这颗痣脱离了身体,就“死亡”了呢?难道说唐毅松看到的,竟是这蝉斑在爬动?
那医生看段杏芳凑在显微镜跟前久久不动弹,害怕出什么问题,便用手推了一推。哪知段杏芳正沉浸在恐惧中,被医生这么一推,陡然尖叫起来,把那医生吓得一下子仰跌过去,撞翻了一个吊水用的挂架。 那医生姓田,性格还算蛮好,不怒反笑:“怎么了?显微镜里还能看到史蒂芬·金?”
段杏芳结结巴巴说:“我的痣里面……好像有只‘知了’……”
田医生一愣,走上去,段杏芳让到一边,田医生盯着显微镜看了很久,段杏芳感觉脚都站麻了,田医生才抬起头来,盯着段杏芳缓缓说道:“你知道幽灵吗?”
段杏芳摇摇头,田医生走过去关上病床门,示意段杏芳坐在床上,他很是兴奋地侃侃而谈:“你知道吗,我以前喜欢收集古籍,在一个旧书店买过一本很古老的线装书,那上面说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化成魂凝成魄,而冤死之人就没那么简单,他们在死之前会有一股无法解脱的执念,这股执念会变成幽灵附属在冤魂之上,幽灵因为只是单独的执念,所以它可以演化的相态取决于执念的内容,它附属于冤魂却又不受冤魂控制。如果幽灵撞见和这执念相关的物事,都会在其身上留下烙印,烙印的方式有很多种。”
(晕,原来幽灵是这个东西,到有些类似日本人说的‘怨念’,这理论真强大~)
段杏芳头皮发麻:“你说这个痣……是幽灵的烙印?”
田医生嘿嘿一笑:“那书上说,痣也是烙印的一种。所以说幽灵无处不在,有多少人会去留意自己身上的大痣呢?你这个痣里面的行走像蝉,证明这股执念和蝉有关,你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和蝉有关的事情……”
田医生口若悬河口沫横飞,段杏芳却越听越心惊,连带看这个医生都觉得很恐怖,她强自压住心中的恐惧,平静地骂了一句“胡说八道”,“若无其事”地走出医院。
一出美容医院的大门,便落荒而逃回了家。
到家翻出那枚玉蝉,左思右想,总觉得一系列厄运和这玉蝉大有关联,要不怎么痣里也有蝉的图案呢。这玉蝉一定是不洁之物,她决定甩开玉蝉,把厄运转嫁给别人。
所以,她去了黄拐子的猫肉馄饨店,悄悄把玉蝉和在馅料了包了个馄饨。
事情就是这么巧,这玉蝉竟然又被她新认识的姘头唐毅松得了去。 段杏芳的故事迂回曲折,骇人听闻。那个神秘的田医生,怎么会那么清楚什么幽灵的事情,难道真如他自己说的,都是从古籍上看来的?
从古籍上看来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认真地跟段杏芳讲述。
听起来,好像这个医生倒是小题大做,故事把话题往“蝉”上面带?
段杏芳被吓坏了胆子,这些东西她应该都没有细细分析过,我心说,这个田医生,十分有见面的价值!
在回来的路上,胡知道说:“银子,你说段杏芳嘴里的田医生,会不会是那田福生的什么人?他们可都是姓田啊。”
我心中也是那么怀疑的,我说:“那家美容整形医院我知道,咱们中午和邵大力他们碰个头,下午就去那医院找一下田医生。”
胡知道说:“知道了,也是,现在猜什么也是白猜。”
找了家饭馆,刚刚坐下来,邵大力的电话也就打了过来,我说:“怎么样,见到林宝康没?”
邵大力说:“一言难尽,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说了饭馆的位置,邵大力他们现在的位置离我们这里并不太远,我说正好,一起来吃个饭,下午我们一起去个地方,见个人。
不到一刻钟,邵大力和海洋就来到饭馆。两个人满头大汗,坐下来猛喝两口水,邵大力说:“胡哥,银子姐,你们知道吧,原来林宝康已经死了。”
我和胡知道一怔:“死了?”
海洋接口说:“医院里说,林宝康一个礼拜前就死了,说是什么精神恍惚,从安全通道的楼梯上滚下去死的,七楼滚到二楼,医院还赔了林家一笔钱,所以我们问到林宝康,医院里的人都没有好脸色。”
还是海洋说话比较有条理,我们总算听清楚了,失足从楼梯上摔下,这种死法还不算怪异,我现在最怕听到和阴楼有关的死亡事情,但愿林宝康的死是个纯粹的意外。
邵大力说:“我们问明白了林家的住址,原来就在本市北郊渭塘镇的一个什么村,我和海洋一合计,反正闲着也闲着,不如去林家看看,说不准有什么发现呢?”
我问:“那有没有什么发现?”
邵大力说:“有,那当然有,海洋,把东西拿出来!”
海洋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纸片,那是一张老照片。
照片是旧社会那种全家福,有穿长褂子留胡子的老头,也有坐在木头摇椅上的老太太,还有一堆憨头憨脑的青年男女。我问:“这是什么?”
海阳说:“这是林家祖上的老照片,银子姐,你看看背面。”
我把照片掉了个面,眼前不由一亮,只见右下角依稀有行不清不楚的繁体印章字:福生田记照相馆。
天,竟然是在田福生的照相馆照的。如此看来,田宝康知道田福生这个人就不奇怪了,他祖上一定有人和田福生认识。
可是,当初他带过来的,有着我和胡知道的老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那张照片也是福生田记照相馆出品?我将这个疑问提了出来。
邵大力笑道:“你们要是知道林宝康是干什么的,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胡知道说:“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邵大力说:“他是海报设计师,算得上半个艺术家呢。”
我们恍然大悟,海报设计师,一般来说都是PS高手,熟练试用phothoshop,谁都能造出一张老照片来,更何况,林宝康还有老照片可以参照。
我们只是不明白,他跑到601来的目的何在?
可是,要想弄明白疯子的目的,除非我们也是疯子!
“还有哦。”邵大力说着又献宝似的拿出一卷纸。
胡知道好奇地问:“这又是什么东西。”
海洋说:“一幅画,林宝康死之前一直在画这幅画,这是医院方面告诉林家人的,这幅画也被当成重要遗物送到林家。”
画是用铅笔画的,一张人物肖像。准确地说,是一张古装人物肖像,头戴文生公子巾,面容俊朗,双眉似剑,下巴很有棱角,没有文生的那种文弱书生气,倒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剑客。
我说:“林宝康死之前画这个是什么意思?”
邵大力道:“那哪里知道,他那会精神还是不正常的,也许我们梦里见过那个吓人的古装女子,他老人家梦里就见过这个家伙呢,嘿嘿……”
我们无语,胡知道让海洋先把画收起来,说道:“你们是怎么骗来这画的?”
邵大力又是嘿嘿一笑,洋洋得意地说:“我说我们是孙小姐的朋友,代孙敏来看看林宝康,谁知道林家人深信不疑,还差点留我们吃饭呢,要张照片要张画那有什么稀奇。”
海洋掐了他一下,说:“胡大哥,银子姐,你们在段杏芳哪里打听到了什么没有?”
说话间,菜和饭都陆续端了上来,我们边吃边说,把从段杏芳那里得来的讯息和我们推论一一明细。
邵大力听到吃惊之处,好几次把饭呛入气管,从鼻孔里喷出米粒来。
唉,真是让人大倒胃口。 “怎么,你们不信?”那女人低下头,拆下盘头,撩开头发说,“你们看看。”
这时正好轮船上的探照灯光扫到她们身边,就听众位贵妇齐齐发出一声惊呼,连那个哭泣的女人也不例外。田顺来虽然离得比较远,但少年人眼力尖,也瞥见那女人的发间头皮上,沟壑纵横,尽是刀疤。
刀疤处没有毛囊,所以那女人的头发披散下来看起来一络一络的泾渭分明,很是可怕。
旁边一个女人问:“雅梅,这……这是怎么来的?”
叫雅梅的女人慢慢把头发重新盘起,微微一笑说:“被人砍的,被一个疯子砍的。”
四周的女人们都惊叫起来,那个雅梅的女人满脸得色地说道:“你们都想像不出来吧,好了好了,我就不卖这个关子了,听口音你们该能分辨出来,我是湖南常德人,老实说,我的出身并不好,山村旮旯里的。我出生刚刚六个月的时候,家人在下地干活,就把我放在摇篮里,把摇篮搁在地头山路上,山里人都这么照顾孩子。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个疯子,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伙都叫他的外号——邋遢书生,听说还是个清末老秀才。那天,那个老东西不知为什么原因,举着一把菜刀,冲过来对着摇篮里的我就砍。”
四周的阔太太们都惊呼地捂着脸,田顺来心说,六个月大的孩子,那还不是一刀了结,这女人也太夸张了,不由自主,又靠近几步。那女人接着说:“这老东西足足砍了我二十六刀,我流出来的血把整个摇篮都染红了,地里干活的父母大惊,急忙跑过来,钉耙锄头地赶走了疯子,可是已经晚了,眼见我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连哭声都彻底熄灭了。”
大伙听得大气不敢喘一口,四周只听到江浪拍击船身的声音,雅梅从旗袍衣襟里掏出一方丝巾,执起一端擦了擦湿润的眼角,说:“那时,父母只当我已经死了,果然,到了家里,就断了气。一家人极度伤心,我奶奶却说了句,反正是个女娃,死了也就死了,埋了算。我爷爷当即就煽了奶奶一个巴掌,奶奶不啃声了,赌气回了屋内。我爸妈和我爷爷想想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最后还是扛上锄头去了山腰,刨了个坑,就准备把我埋掉。”
“坑刨好了,妈妈把我放进去,父亲给我填土,几锹土落到身上,爷爷忽然叫了起来,他说看到我的一根手指动了一下。我父母都劝他,说怎么可能还能动弹,肯定是泥土打在手指上闹出的动静。可我爷爷不依,仍旧把我捞了上来,说死马也得当活马医一下才知道,何况是个孩子。爷爷把我抱了回去,找了黑沟泥给我糊满全身,用我们那里的土办法给我处理伤口,屋顶上晒的草药是现成的,草药熬了一锅米汤,从我牙缝里灌进去,给我提神吊命,忙活到半夜,一直抱在爷爷手里的我身子陡然蜷缩了一下,发出一声咳嗽,我这就算二次活过命来。” 田顺来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就在这时候,江面上忽然刮起风来,伴着风来的便是浪,浪打得船身前后左右摇晃,甲板上不再似先前那般平稳。那几个阔太太大惊失色,扶着栏杆尖叫。有几个船员过来扶着她们进舱室,田顺来少年人好奇,故事听到一半哪里肯罢休,想这几个女人回到舱室多半还要接着讲,便大了胆子尾随她们进入贵宾船舱。那几个船员只当田顺来是某个太太道跟班,倒也没有在意他。
甲板上的建筑总共有两层,下层有半数面积是个大的休息厅,里面有留声机放音乐,还有好些桌子座位用来休息喝酒打麻将。休息室里虽说也摇摇晃晃,但一来有座位依靠,而来不用直接面对大风大浪,感觉上要好得多。
那几个太太果然围着一张麻将方桌边打牌边唠嗑,只是那个刚刚死了丈夫的明兰好像没了打牌的兴致,把座位让给了别人,她坐到雅梅的身旁,低着头。继续听雅梅把她的经历断断续续讲出来。
田顺来大着胆子,有模有样翘着二郎腿坐在她们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幸亏应付风浪,船上的工作人员都跑甲板上去帮手了,倒也没侍者来赶他。田顺来竖起耳朵,只听那雅梅继续说道:“你们问什么?那是什么男人?哈哈,我告诉你们,我救起来的男人可不是别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啊。”
肖太太说:“不会吧,雅梅你救了他,他就对你以身相许,怎么听着像张恨水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不信是不是?”雅梅在肖太太胳膊上拧了一把,“不信你下次亲自问我老公去。”
肖太太说:“呦呦呦,你个小浪蹄子,不怕我抢了你的老公?”
看来这个肖太太和雅梅相当熟,雅梅嘻嘻直笑:“你去抢啊,不去不是人。”
一群女人都放浪形骸地笑了起来,其他女人跟雅梅不是很熟,都和肖太太打听:“雅梅先生是什么来头啊?”
肖太太说:“雅梅福气好,他先生是戴老板,全中国最大的湘绸商人,绸布都卖到军队里去了。”
一行人啧啧赞叹,田顺来没听说过戴老板这个人,但看众位太太一脸羡慕的表情,显然这个戴老板是位豪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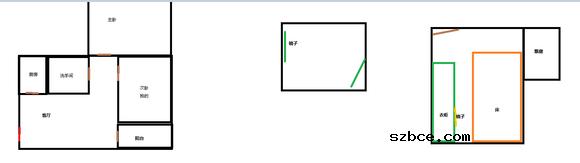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